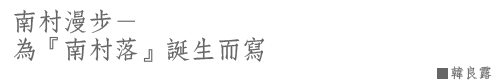美好的都市,應當是由許多個性不同的村落組成的地方。
譬如說倫敦,當地人都會說,倫敦不是都市計劃生出來的城市,倫敦是由上百個村落獨立生長出來的有機體,才慢慢形成大倫敦的概念。
倫敦人覺得好的居家住所。一定得有自己的村落特質。譬如肯明頓村落。混合著波西米亞、龐克、左派知識份子的氣味,譬如說諾丁山丘,混合著加勒比海移民的粗放和時尚藝術家的風格,又譬如我在倫敦居住了五年的貝斯華特村落,雜處著猶太、希臘、中東、亞洲、愛爾蘭人,彷彿一個鑲嵌多元文化的珠寶盒。
我在不同的城市流連忘返時,選擇或長或短的居處時,都會待在有村落味道的地方,像在巴黎,我一定住在聖日耳曼或西堤島的小巷小弄之中,在舊金山時,我常住在北灘的義大利村和法國村之間,在紐約時,最理想的居處當然是格林威治村和東村,連在洛杉磯這麼可怕的怪獸都市中,我都可以躲藏在帕薩迪納老城區的綠蔭村落之中。
在台北長大的我,小時候住在北投,北投是一個到今天都仍有村落特色的地方,有許多互相認識的老居民,黃昏時還有居民敢穿著汗衫拖鞋滿街漫步,這種有些落後閒散的氣息是台北東區居民無法想像的環境。
從倫敦返回台北後,我一直住在天母和北投之間的地方,想同時兼顧離北投老家近的念舊與離天母繁華商圈近的便利,但住著住著,卻慢慢覺得住在十八樓高的我,雖然有大屯和陽明的山景可看,但卻似乎離我理想的村落生活有點遠,我的內心有一種渴望,想離土地近一點,想離一些每日可以走來走去的咖啡店、書店、花店、雜貨店、傳統市場、小酒館、小餐館…等近一點,想住到一個地方,那裡做開店生意的人,是你會想交往的朋友,他們開店不只是在 earn money,也在earn a living(賺一份生活)。
一年半前,我搬到了南村。這個眾人稱之師大商圈的地方,被我在內心中改了名字。在住商混合的台北市,最好任何地方都不要太商業化,因為都市居民的住所應當是為人而服務而不是為商業服務,每個地方都需要保留獨特的村落文化,應當是都市村落,而不只是商圈。
住在南村後,我又恢復了成天走來走去的習慣,彷彿閒散的村人,心中沒什麼目的,推開家門就進入了村子,隨處晃晃,東看西看,久而久之許多景物在眼前一過再過,慢慢地就有了不同的意義和味道。
有時,起個大早,走出家門的小巷,看到24小時不打烊的JR酒館前有些喝了一夜酒後恍惚的客人,竟然在草地前小解於天地之中,路旁的野狗望著他頗有同類之感,在此清晨薄霧迷離之際,也不覺酒客有所失態。師大藝術公園(我都稱之為南村公園)前的涼亭,週末清晨偶爾一些膚色黎黑的外籍工人在此彈吉他唱歌,臉上還有整夜的酒色,他們的歌聲粗放而直接,聽得出都市生活的苦悶,只有在南村這樣的地方他們才能有所放鬆。
像水蛇般蜿蜒的龍泉老市場,清晨的早市忙絡起來,還淌著露水和土泥的絲瓜、綠竹筍、空心菜、莧菜堆滿了巷道,偶爾還有小攤賣著山區摘來的各式野菜。市場內響著民以食為天的庶民談話,主婦睜著大眼瞧著魚眼,盤算著對方的身世,魚攤上寫著產地來歷,只是沒記載魚兒的家鄉是那一方的海水。
我提著小籃子買丁點兒的菜,跟市場住得近,有閒心時,一天可以上兩三次市場,每次都只買最時鮮的菜,買回去了後就可以下鍋,冰箱就留著冰乳酪、火腿、果醬、水果就成了。
早市後,可以到一大早就開門的義式咖啡店Trobetta去喝一杯手搖冰咖啡,這家被我稱為義大利小歇的地方,咖啡的味道和我在義大利大城小鎮的市場、小店喝到的冰咖啡一模一樣,在這裡咖啡並無任何人文、哲學、藝術或革命的附加意義,咖啡就只是咖啡,是生活,是飲料,單純的好喝。
有時,我會在中西美食二樓的露台上,對著繁茂的九重葛,吃著嗜辣的我灑上好多的Tabasco汁的墨西哥早餐,這裡週末我是不來的,因為會大排長籠。
早上散步的遠時,會經過溫州街台大教職員的日式平房的老宿舍區,經過殷海光、臺靜農的故居,想到有一回北大的教授友人來訪,在大雨滂沱中,對方聽我提起殷海光故居,執意要冒雨瞻仰已成荒園之所。真是文人之心。
南村還有梁實秋故居,在離我家不遠的雲和街上,日式老屋的屋瓦已成破落的窟窿,我散步時經過這裡時想著若老屋若修復成雅舍書齋該有多好。散步時我最喜歡的地景,是浦城街上老樹爬藤蔓生的石牆,如此強韌的生命力的叢結,後來我在構思「南村落」的圖騰時,自然就選擇了這個意象。
不做菜的日子,南村有許多可以打食的地方,譬如說去帶著大白狗一起賣披薩的瑪莉珍,吃手工的瑪格麗特或四種乳酪披薩,或者去愛畫畫的女人開的鹹花生吃簡單的早午餐,聽許多喚起我青春鄉愁的音樂,我是屬於鹹花生的午後客人一族的,可以一人獨佔一張大桌子寫稿看書辦事,完全自在如在自家書房中。
住到南村後,偶爾午後不在外打混時,會賴在家中午睡,伴著我入睡的音樂總是蘇州彈詞或泉州南管,悠悠忽忽躺在客廳上的沙發入眠(最舒服的午睡總是在沙發上而非床上)。
睡起時想喝一杯熱熱的卡布奇諾時,會出門看看老鼠窩開店了沒,這家不到三坪,一樓坐五人就擠爆了的小咖啡主人開店沒定時,也許下午三點開店也許不,要去碰碰機會,我總慫恿主人賣早上站著喝的義式咖啡,說了也是白說,晚上是老鼠出來活動的時間,因此店通常開著,但我晚上不喝咖啡,只好夜夜為了串門子去那喝比利時水果啤酒。
有時,下午也會閒步到時光書頁停留處的舊香居,去和女主人卡密說長道短,在滿屋舊書陳香的空間中,卡密本的存在能讓不少老書虫精神振奮。偶爾我會買一些幾十年前出版的地方誌、戲曲之類的老書,買來滿足在我內心深處躲藏的那個不合網路年代時宜的我,在舊書店的我剛好處在不老也不年輕的客人中間族群,偶爾觀察一些年輕人買老書還挺有意思,像有一天下午,一位打扮得如同穿著Prada的時髦女孩進來,問是否有「人間雜誌」?我忍不住問她為何想買,竟說十分喜歡這份當年標榜社會主義觀點的報導攝影雜誌,人說有沙發社會主義者,但當Prada社會主義者其實也很不錯。
黃昏時南村的人潮開始多了起來,龍泉街開始熙熙攘攘,南村的腸胃蠕動著,我在古早茶舖喝青草茶,聽身旁兩個女孩聊天,說起到英國里茲唸書,想起夜市的蚵仔麵線、鹽酥雞、糯米腸包香腸、臭豆腐、甜不辣都快想瘋了,台灣人的愛國意識其實不是腦決定而是味蕾。
自從賣甘蔗汁的小發財車主人帶著他的白鵝一起在黃昏上班後,黃昏漫步時我總是不會忘記去和白鵝打招呼,這隻鵝是最認同南村是村落的生物,自在的在人行道上踱步,天天看鵝使我開始不吃最愛吃的燻鵝肉了。
南村的黃昏有些蠢動,Vino Vino前的棕櫚樹已經成為村落約會的地標,常常有各種老外坐在人行道上喝啤酒,小孩和狗在公園遊樂場玩,Vino Vino那隻得皮膚病帶著白頸圈的大白狗鬱卒了好幾個月,只能在旁不安地扭動身子。
有的晚上,通常不是週末,我會去blue note喝一杯Single Malt,聽一會爵士樂,想起我在二十幾年前東京高田馬場的早蹈田大學附近聽爵士樂的往事,還有紐約的Village Vanguard和倫敦的Ronnie Scott,爵士時光一直是夜之殿堂。
不知從何時開始,師大路夜市口每週五晚都會有流動搖滾樂團在那演唱,聚集聽音樂的人還不少,這裡也許可以成為日後南村街頭表演節的固定會場,是南村小小的春吶。
深夜的南村,慢慢地又沈澱了下來。夜市人少了,只剩下一些夜貓窩處在柏夏瓦小咖啡館裡聽世界音樂喝越南咖啡,鹹花生的夜充滿狂野的青春荷爾蒙,morelax是南村超級吸煙室,深夜兩點抽煙的年輕人都埋著頭在打電腦,很少人互相交流,這裡是南村的虛擬村落。
南村最奇異的景象,是從早開到晚深夜一點還不打烊的皮膚科,真有這麼多人有皮膚問題嗎?我的弟弟從美國回來,看到此情景卻大嘆好命,不像他若要看皮膚不只要先預約還得開上兩小時的車。
不常在深夜散步的我,偶爾在東區的夜店玩瘋了深夜才回南村,走在寂靜的小巷小弄,總有一點回到了心靈的家的感覺,覺得沒有住在高樓大廈真好。
南村於我,像海明威說的巴黎般是一場永不停止的盛宴,在這裡慢慢老去的我,常常會以為自己其實並不太老。
南村這樣的村落,是台北人心靈的後院,是一個可以在清晨散步黃昏漫步午夜沈思的家,這裡成為「南村落」的起點,於是2007年6月22日夏至夜,南村落在南村誕生了。
|